
文/杨向荣
原刊于《书城》2020年11月号
1一1

狄更斯(CharlesJohnHuffamDickens,1812-1870)
狄更斯(CharlesJohnHuffamDickens,1812-1870)大概是十九世纪英国作家中最现代的现实主义作家。正是这点延续了他的小说的生命,让我们把他的小说从他本国的《弃儿汤姆·琼斯史》这样的长篇中辨识出来,也跟《十日谈》和《堂吉诃德》《巨人传》之类的古典小说区别开来。这种鲜明的辨识度就得自他的现代性。很难说他有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那样自觉的现代意识,他的现代意识介于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时代审美潮流的限制使得他无法大步走向现代性,这种羁绊留在他精确的现实主义中的时候,就让他的小说跟同时代的萨克雷也有不同。他的现实主义中渗透着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好像来自他直觉的现代性而不是来自理性的现代性。我们随便抽取他的句子来读,就会发现那种气质没有某个过去特定时代的局限,似乎出自今人之手,除了内容,比如伦敦街头的煤气灯。读契诃夫的短篇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契诃夫和狄更斯都超越了他们的时代。
我记得很早之前读过王佐良先生谈狄更斯小说的片段,先生对狄更斯只说了几句话,但却引述了《荒凉山庄》里很长一段关于雾的描述。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主万、徐自立先生的译本中找到了王佐良先生的这段引文(当然王先生用的是自己的译文),我想这可以算是狄更斯具有现代意识的一个小小证据:
我想,作家们要把雾搬进小说的时候,有的可能只用寥寥数笔,有的可能会用几句对偶的诗词,如中国古代诗人的“雾失楼台”,在现代小说兴起之前,雾好像鲜有获得独立地位的机会,但是狄更斯在这个细节上却不管过去的窠臼,放开笔墨来专写雾的弥漫,写雾如何无远弗届,又如何神出鬼没地流动,在想不到的地方出没……我把它理解为狄更斯在事物描写上现代性的萌动,准确与诗意在这里获得了恰到好处的交融,正如雾中万象皆备,什么都有。一个多产的大师在雾的描写上如此不慌不忙,大肆铺展笔墨,不怕奢靡,不肯匆匆收笔,直到他感觉心满意足方休,终于这雾也钻进了读者的眼目耳鼻。所以,王佐良先生说他最奇幻、最夸张,在渲染、烘托上最走极端。
王佐良先生在说狄更斯的描写还有某种尖锐性的时候,举了个我永远难忘的例子。《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去见继父的妹妹,这位小姐“只将冷冷的手指甲让孩子握了一下”。我想,作家得有多么敏锐和尖锐的感觉才能写出只握了握指甲这样的细节。那位小姐可能经过独特的操作很容易做到只给指甲握握,但是让作家想出这样的握法,看似很小很小的动作,没有大智慧,没有天外飞仙般的灵感,其实真不见得能办到,因为这个世界上可能压根就没有哪位小姐让小孩这样只握握她的手指甲,有可能这就是狄更斯想象出来,然后世界上第一次有了这样冰冷的握手分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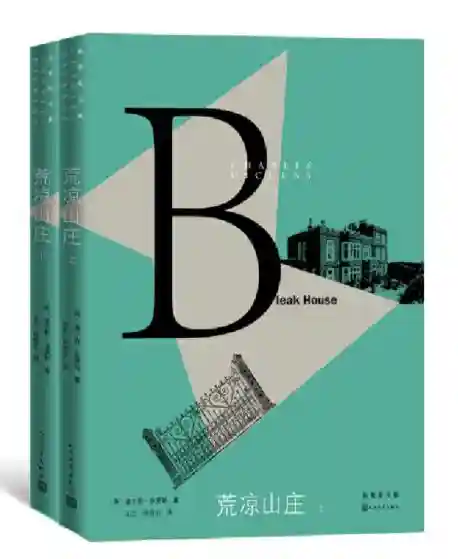
《荒凉山庄》
主万徐自立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1二1
让我惊讶的是,狄更斯年纪轻轻写出来的作品就已经非常广博厚重了,即便有瑕疵也掩饰不了一块块砖头般的东西搁在眼前的物理事实,那瑕疵也是砖头上的瑕疵。很多作家到了五十岁才有的厚重或者说伟大,狄更斯年轻时就已经有了。单就长篇小说而论,他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从一八三四年开始连载,时年二十二岁,这本小说直到一八三九年才连载完,完成时二十七岁。《匹克威克外传》从一八三六年开始在杂志上连载,一八三七年完成,开写时他只有二十四岁,完成时二十五岁。有些作家在这样的年龄文笔可能还很稚嫩,对文学的操练可能还停留在服侍抒情和讨巧的篇章上,也许偶尔写点出色的短篇,但驾驭类似《匹克威克外传》那样规模庞大的鸿篇巨制,我依然觉得对一般人实在太难了。狄更斯写了伦敦一个俱乐部成员在英格兰四处游历,遭遇的各种戏剧性事件,在主人公匹克威克身陷囹圄后又让情节在更大的范围展开,走进复杂社会生活的腹地,这种老练成熟跟二十四岁的年纪实在太不相称。如果统计下著名作家在二十四岁左右都写过什么,我们就会发现狄更斯有多么了不起。《匹克威克外传》还在连载之际,《雾都孤儿》已经开写,并于一八三八年连载完,其时狄更斯才二十六岁。(这本小说写的是十八世纪的事,虽然他本人距离那个时代并不遥远,正如我们距离二十世纪并不遥远一样,但是写那样一部犯罪小说需要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尽快加工剪裁成形,不是借对当下的感觉描写就能轻易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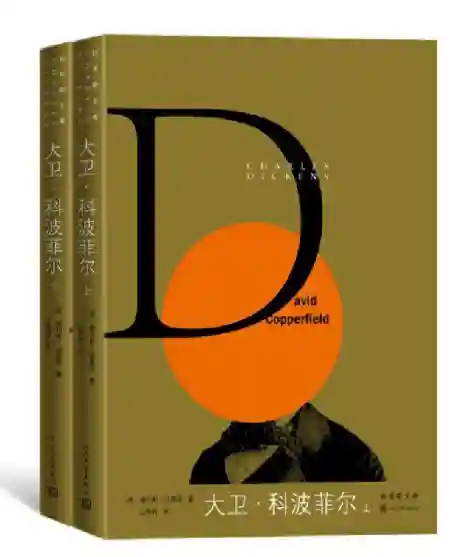
《大卫·科波菲尔》
庄绎传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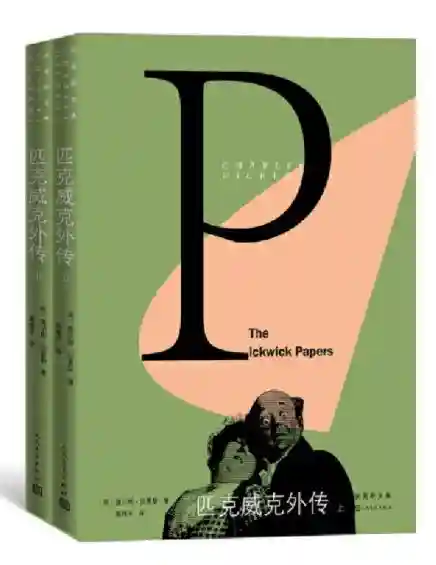
《匹克威克外传》(上下)
莫雅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我们说狄更斯年纪轻轻其处女作就具备了伟大的气象,还因为这部作品创造出了三百个左右的人物,他们群集在匹克威克的世界,这些人物的活动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细节。这个世界是活动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天真而必然会闹笑话的匹克威克先生及其信徒们漫游走出来的世界。我们无法想象这不是一个嘈杂喧闹的世界,很难想象一部扎实的现实主义作品寂静得像无菌的温室,连蜜蜂的嗡嗡声都听不到。这些人物举止怪异,行为难测,念头荒诞不经,语言刁钻,出其不意,构成人间的种种笑闹。然而,狄更斯在讲述喧闹和可笑时用的却是低调克制甚至严肃的口吻,反而强化了小说中发生的事件的幽默性,让人哑然失笑。众多荒唐的人物加上同样被作者赋予荒谬性的无生命物体,撑起这部小说的世界。
1三1
狄更斯无论如何驰骋其天才和智力,如何随心所欲地搅拌和剪裁素材,如何创造了一个社会万花筒般的仙境,他都是在现实世界这个巨大无比的画幅上挥毫,或者消耗其才智。他在驰骋的时候动员了因此也穷尽了各种才智和情感。他带领我们穿越形形色色的万花筒仙境时,没有老实地用单一的理性或者单一的情感来描写这些社会仙境,而是时而搞笑,时而伤感,时而恐怖,时而批判,时而博爱,时而讥讽,时而锋利如剃刀,时而深刻如哲学。至于何时用什么样的时而,完全取决于他到达了万花筒的什么境地,以及他的智力在那个时刻允许他做出什么样的发挥。幸运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时而有太多斧凿的痕迹,虽然他已经如庄子向往的那般运斤成风。我想这就是大师的成熟智慧,虽然这个大师只有二十四岁。
我们众口同声说狄更斯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时候,恐怕对他天外来仙般的非现实主义要素有所低估。现实主义常有,批判现实主义亦常有,天外飞仙般的非现实主义则不常有,那部分可能决定了狄更斯作品的魅力。狄更斯的人物是社会万花筒中的人物,与其说他给了我们一台显微镜,他更像是给了我们好多个万花筒,在喧闹的万花筒里,他的人物穿着现实主义的外衣,但幻化出无限的璀璨变化来。
1四1
正因为狄更斯时刻站在社会现实中,时刻把目光投向活的人生,特别是投向底层人的生活,所以他那独特的夸张和剪裁对社会的批判或者讽刺就显得格外掷地有声,刀锋直接走向社会现实断裂的缝隙,撬开社会黑暗处的景象,破开人性中残忍的地带,刀锋所指反而比记者的记录还要准确和犀利。狄更斯犀利的人性讽刺和社会批判的效果并没有用正儿八经的方式呈现出来,予以实现,很多时候用了讽刺和喜剧的手法,这样的论说浩如烟海,已经无须赘言。我想说的是,狄更斯首先是个有追求的作家而不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家,如果他的写作只停留在理念层面的批判,他作品的魅力不会传之久远。从《匹克威克外传》成书发表到狄更斯去世的三十多年间,狄更斯是他们那个时代活着的作家中最负盛名的,有人说他最受欢迎的时间总共持续了半个世纪,然后才逐渐降温。持续半个世纪的流行已经颇为可观,但狄更斯没有像很多流行作家那样昙花一现,他的作品至今还在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读者。在我看到的有些大作家写的小说中,不时出现某个年轻的主人公在尘封的阁楼上发现了祖父或者父亲留下的成排的狄更斯的作品,或者在学校图书馆中撞到了狄更斯的世界。狄更斯作品长久的生命力,来自他的文学而不是来自他的批判,来自他的技艺而不是来自他的理念,来自他的良知而不是来自声嘶力竭的口号。我们中国读者在阅读狄更斯的时候首先要洗却从教科书得来的先见,首先要祛魅。狄更斯固然描写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经济制度乃至司法的黑暗,但他也描写了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复杂人性。道德良知和文学的技艺,这两点更需我们普通读者去关照。
狄更斯的批判色彩源于他的良知,技艺主要源于天赋,但来路更加复杂,细究起来力有不逮。作为貌似批判者的狄更斯,学力既没有到哲学家的地步,也没有到社会学家的程度,难以去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研究社会经济现象,进而对自己看到的各种社会不公和黑暗进行理论总结,给出原因,给出批判的武器。狄更斯童年的不幸或者磨难让他本能地在自己的小说中去表现别人的不幸和磨难。这个大概就是他那并不十分自觉的批判的原初动力。与其说他是个批判者,不如说他是个道德家;与其说他是个道德家,不如说他是个有良知的观察者。狄更斯十九岁就开始做记者,做报道,他对社会现象的报道不是从理念或者理论入手,而是从现象本身入手,从经验入手。他看到了什么,就写什么,没有让先入之见破坏他的观察记录。但是狄更斯的技艺天赋又并不满足于纯自然地记录观察所见。良知,观察,记录,再创造,自由超越,这些要素的复杂搅混,最后造就了狄更斯可以不断阐释的文本。
虽然狄更斯的桂冠上被理论家和史家写着“批判”二字,但是他本人在多大程度上是个自觉的批判家,还有待论说。幸亏他没有彻底自觉。只有不刻意遵从某种功用主义理念或者不以载道为目的自由创作才可能让社会和人性的广阔与多样艺术地呈现出来,否则读者看到的可能就是被某种道提前剪裁过的僵化的作品,缺少自由自在的波澜壮阔,缺少鲜活生活的灵动,貌似一切皆有意义,实则一切意义皆乏味。我们在阅读狄更斯早期的小说时,明显地感觉到年轻狄更斯自由创作的快感,这种自由的快感竟然使他的叙述敞开有余而收束稍欠,使他的个别早期作品在结构上不够精致,话语滔滔不绝而情节的脉络难免枝蔓杂生——但是狄更斯天才的直觉又能及时控制住这类过于自由所衍生的瑕疵。
1五1
在有关狄更斯技艺的标签中,说得最多的是“想象现实主义”。这是跟贴上“批判现实主义”性质不同的行家贴出的标签。或许这两个标签各管各的行当。前者管形式,后者管内容。我们之前就说过二十岁出头的狄更斯出手就是七十万字的长篇,里面的内容,不管是真是假,复杂广阔到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童年经验是有限的,成年观察是不够用的,道听途说是捉襟见肘的,只能来自惊人的想象力。有人说就想象力的杰出程度而言,莎士比亚都在他之下。这点我相信。在他那些流浪汉式的小说中,简单明确的主线中不断地派生出新的支线,这些支线就是活跃不竭的想象力抽出来的。狄更斯异想天开的能力实在惊人。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狄更斯又害怕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因为他始终不肯绝对地飞到天上驰骋而不落地,相反,他设法不要离开大地,不要离开资本主义社会,不要离开伦敦煤气灯、形形色色的街道和店铺,不要离开贵族的深宅大院,不要离开平民和穷人活动的场地。如果说狄更斯的想象力是不知疲倦四处飞翔的蜜蜂,这些蜜蜂其实还是在街巷里弄中飞来飞去。世界上不缺奇幻故事,缺的是想象力与现实的结合。想象力脱离现实,带给想象力的只能是飘荡,然后在精疲力竭之后从虚空中跌到地上,摔成碎片。狄更斯对这样的脱离深为警惕。
狄更斯不仅是个想象家,而且是个交响乐式的想象家。他的想象不仅仅动用感官中的某一个,而是全能全要素。他调动眼、耳、鼻、舌、身、意全要素去从记忆中捕捉过往的一切细节,来开发此刻的细节。他的奇妙天才即全要素想象不仅体现在他所写的单件事物中,也体现在他的作品整体中。他的句子可听可感可触可嗅,他的世界同样可听可感可触可嗅。这种鲜活逼真有时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他处理微观事物和宏观世界几乎用了同等的力量。他对于自己陌生的行当活计的精确想象甚至超过了行当伙计所能描述的程度。那真叫体物入微、传情入神。
即便我们跟狄更斯听到同样的声音,看到同样的色彩,但形诸笔墨时,狄更斯必然要强调,必然要使之尖锐化。这是他的本能敏感使然,他非要这样不可,平平淡淡的再现必然令他不适和焦躁。但是,奇妙的是,狄更斯的这种强调和锐化,并不影响他想象力的精确。相反强调和锐化强化了精确。这就像有时强调和夸张的漫画比照片还要更加准确传神。照相式的现实主义和漫画式的现实主义,哪个更准确地反映现实呢?估计在伯仲之间。狄更斯的想象力或者本能,让他能越过理论或者概念直达真理或者真实。这是天分使然。
1六1
在文学作品中,人性是很难人为杜撰和创造的,作家所能做的其实主要是发现、挖掘人性固有的复杂性,然后艺术地呈现出来,并且看上去合理可信。好像没有人统计过狄更斯的十几部规模庞大的长篇小说究竟写了多少人物,那一定非常可观。更加可观的是,他的这些长篇小说也是人性多样性、复杂性和微妙性的百科全书。如果残忍是人性的负面要素,那么残忍也有各种各样的附体和搭配,有怯懦的残忍,有激情犯罪式的残忍,有无知的残忍,仔细探究下去,人性中某个小侧面都可以派生出众多更小的侧面,我所谓人性的多样复杂微妙是指这个意义上的。狄更斯世界中的芸芸众生正是形形色色人性的载体和附体,各种人性及其侧面都可以在他的小说中找到样本。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小说是人性多样性的百科全书。
狄更斯是在真实中,在社会现实中呈现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所以他笔下的人性充满了动态性,不是诸种性格配方的组合。比如在《雾都孤儿》中,南希对凶狠的强盗就充满了忠诚爱慕,按照常态的逻辑,像南希那样的姑娘就不该对赛克斯产生温情,而赛克斯几乎可以说是个绝情到底的人,有着完全不可救药的冷酷无情。面对有些人对这些人物的异议,狄更斯亲自在这本书第三版的前言中做了澄清:他只忠于真实,真实中有什么样的人物和人性,他就写出来。狄更斯说,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指出严酷的真实,甚至在描写被盛赞的人物时,都是如此,他声称对自己的读者并不隐瞒南希蓬乱头发里的一张卷发纸,只要对真实的现实有过观察的人,就知道南希的行为和情感活动没有丝毫夸大其词和牵强附会。“这是神圣的真实,因为上帝把这个真实留在堕落的和不幸的人的心中,他们还有一线希望,在长满青苔的井底还有最后的一滴清水。真实中既有我们本性中较好的,也有较坏的一面,大多数是它最丑陋的特点,然而又是最美的;这是矛盾,是看上去不可能的反常,然而这是真实。”狄更斯在这里已经把自己对真实中的人性状态讲得非常清楚了。他的其他小说中人物的人性呈现也遵从他所谓的真实这个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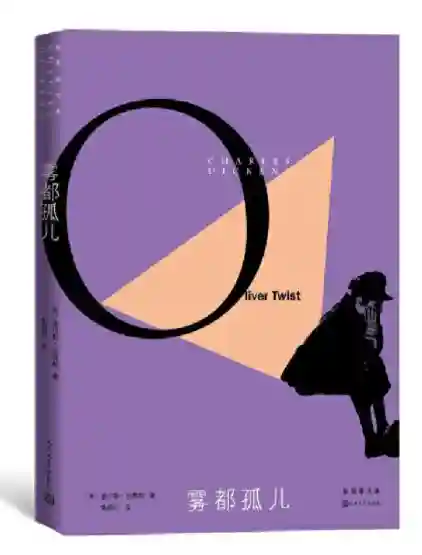
《雾都孤儿》
黄雨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以狄更斯对社会和人性的洞悉,他不仅善于展示人性的多样,在他的中后期作品中,他的人物所经历的人事也并非一味地善或者一味地恶。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就始终贯穿着善与恶的平衡,以及二者的互相依存。在大卫悠然的童年时代过后,接着而来的是寡母嫁给生性恶毒的摩德斯通先生,此人在教导和培养大卫性格的掩护下,利用彼此的感情作为折磨大卫和母亲的手段。这种好坏交织的命运,好人坏人交织出现,没有恶的出现,后面的善又不会引出来,这样的景观构成这部小说的显著特色,很难说它在道德意义上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或许这样的良莠交织才更像生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董贝父子》也有这样的认识。
1七1

凡人物皆有活动场所,凡事件皆有发生地点,狄更斯对地方和空间往往都不含糊而过,有些地点场所是其虚构,有些实有其地。酒馆、旅店、教堂、法庭、工厂作坊、大街小巷、剧院、医院、监狱、学院、政府机关、码头、私人宅院、花园、贫民院,加上在这些场所活动穿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狄更斯的外部世界,这已经够复杂了,再加上其中人物各不相同的气质、命运,让狄更斯人与物交响的内在世界更加活泛和幽深。

塞缪尔·劳伦斯为狄更斯创作的肖像(1842)
狄更斯写外物,写伦敦的一切,写云雾雨电,均绝非脱离自己的主观感受,进行纯客观的描摹经营,而是带上自己的主观点染。比如他写煤烟从烟囱里出来,就说那是一阵淅淅沥沥的黑色细雨,然后又突然加进一句:“人们也许会想象这是为太阳的去世表示哀悼。”突然飞来这么一笔,又把外在的客观情景带到更逼真的氛围中去。狄更斯的外物具备纯外物的表象,气质中却渗透着相当有力的个人意趣的关照。这大概与狄更斯的想象现实主义创作思路一脉相承,他用想象和现实同时建构自己的伦敦。
狄更斯年轻时帅气美秀,灿烂的形象中散发着对生活的热情和一种审慎态度,我的依据是一个叫丹尼尔的画家给年轻的狄更斯画的一幅肖像,虽然这样的判断不够科学。随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事业的深入推进,他的形象也渐渐获得了与其从事的文学事业相当的模样。无论是他年轻时候的形象还是成熟以及晚期的定格看,他都是一个正派的人,甚至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对十九世纪的英国黑暗和不公进行犀利的描写和批判。同样,天才自有其复杂性,老狄本人的世界没有那么简单。人性的复杂在老狄那里也同样难免。无论如何,狄更斯是个热情温暖、生气勃勃的人,更不是那种心中愁云密布、多愁善感的人。他对穷人真正热爱,对穷人的事业真正热衷,很多收入捐作公益。但是,狄更斯本人的生活却并不那么乐观。二十年的婚姻以分居结束,七八个孩子四散在世界各地,大多令他失望。天妒英才,五十多岁他就开始患病,形象已经提前老迈,然后又遭遇一场火车车祸,晚年不听劝告,执意去美国四处朗读自己的作品,消耗了患病期间本该保存的精神和能量,终于,他在创作自己第十五部长篇小说《德鲁德谜案》时中风去世。如果天假以年,狄更斯或许会有更多伟大的作品出来,给世界文学宝库增添璀璨。尽管如此,狄更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已经是不可估量的,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他被广泛认为是英国作家中名望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大师。
【有声书套装】狄更斯文集(8部纸书+3部有声书)
限量5套订购从速!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
shijiewenxue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外国文学书单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一季度外国文学新书





